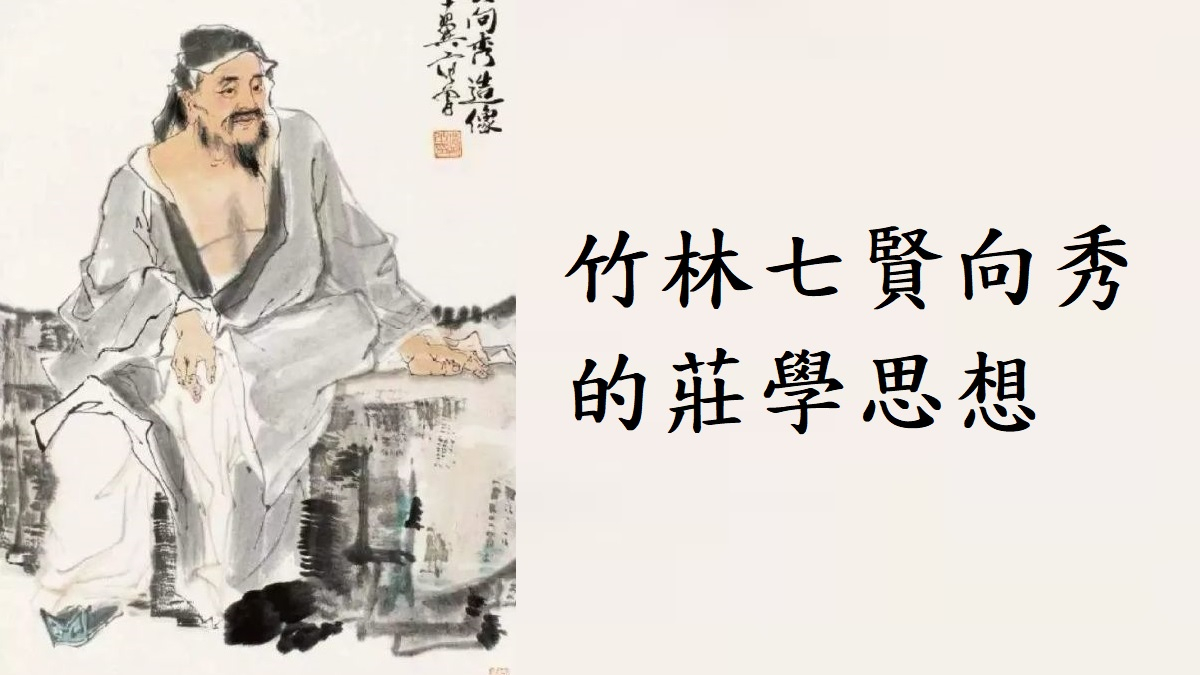郭象注《莊子》是中國思想史一段公案。據《世說新語.文學》:
初,註《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於舊註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唯《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秀卒。秀子幼,義遂零落,然猶有別本。郭象者,為人薄行,有俊才。見秀義不傳於世,遂竊以為己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眾篇,或定點文句而已。後秀義別本出,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
郭象注顯然剽竊自向秀。
牟宗三在《才性與玄理》中指出:
至今只有郭象注,而無向秀注。實則『其義一也』,只是向注。
若郭竊向注,據為己有,則今之郭象注,其大義固只是向秀之思想。
本文談〈逍遙遊〉和〈齊物論〉注解,一律視之為向秀個人思想,而不看成是郭象獨見創獲。
在注解〈逍遙遊〉和〈齊物論〉的過程中,向秀發展出一套系統的莊學思想,涵蓋宇宙論和人生論。
(1) 宇宙論
向秀主張無頭的、氣化的宇宙論,經驗世界背後無另一超越的主宰。西方基督教傳統有上帝創造萬物之說,中國儒家有天道創生的講法,向秀卻將「天」的創生實體地位解消,「天」不過是「萬物之總名」。
另外,他認為物各自造。所謂物各自造,是指萬物自己顧自己地生長,但又互相影響,謂之「獨化」。馮友蘭解釋「獨化」:
萬物不是任何造物主所造的,可是物與物之間並不是沒有關係。關係是存在的。這些關係都是必要的......每一物需要其他的每一物,但是每一物的存在都是為它自己,而不是為其他的任何一物......物與物之間的關係,就像兩支同盟國軍隊之間的關係。每支軍隊各為它自己的國家而戰,同時也幫助了另一支軍隊,一支軍隊的勝敗不能不影響另一支軍隊。(《中國哲學簡史》)
這可視為對向秀見解進一步說明。
(2) 人生論
向秀認為,人之所以痛苦,在於「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惡人」,加上執持自己的偏見以放縱自己行為,於是導致身心俱疲。
要離苦得樂,有兩個重點:任自然而忘是非、性足為大。
「任自然」也者,「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即擺脫日常感官經驗的糾纏,也不去作認知思慮上的種種區分,順乎自然本性而行。
「忘是非」不是要破除、廢棄是非,而是明白世間所有是非標準都是相對的,各自有其合理性和局限,兩邊都予以肯定、順應。與其互相對辯,鬧個面紅耳赤,不如「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和之以天倪,安其自然之分」即明白世間種種是非皆有其成立的理由,亦有被駁斥的不足。佛家般若空宗講「不壞假名而說諸法實相」,跟向秀「不壞是非而說泯去是非」,思維上是十分相似的。魏晉玄學率先契接佛家的般若空宗,是有理論上的原因。
「性足為大」,指安於自己的性分,不去逾越,不作非分之想。向秀說:「臣妾之才,而不安臣妾之任,則失矣」、「夫臣妾但各當其分耳,未為不足以相治也」。由於主張「性足為大」,槍榆枋而止的蜩與學鳩亦不能說不逍遙,向秀因此說:「苟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最後,好生惡死純屬認知上的偏見,只要明白「物化」(事物隨時日推移而變化) ,便可看破生死。
《莊子》〈齊物論〉中確有「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教人不要執著自己主觀的是非標準。〈大宗師〉亦有「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與向秀「遣耳目,去心意,而符氣性之自得」相契接。
不過,〈逍遙遊〉中,莊子清楚是不屑蜩與學鳩,而發「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之嘆,他怎會認為蜩與學鳩都能夠像大鵬般逍遙?又蜩與學鳩都可逍遙,積厚工夫從何說起?「性足為大」、「適性逍遙」未必是莊子想法。
至於無頭的宇宙論,〈大宗師〉有「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道既然先天地有,生天生地,向秀的說法似乎不合莊子本意。
David Lai 香港中文大學文學士,喜歡文史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