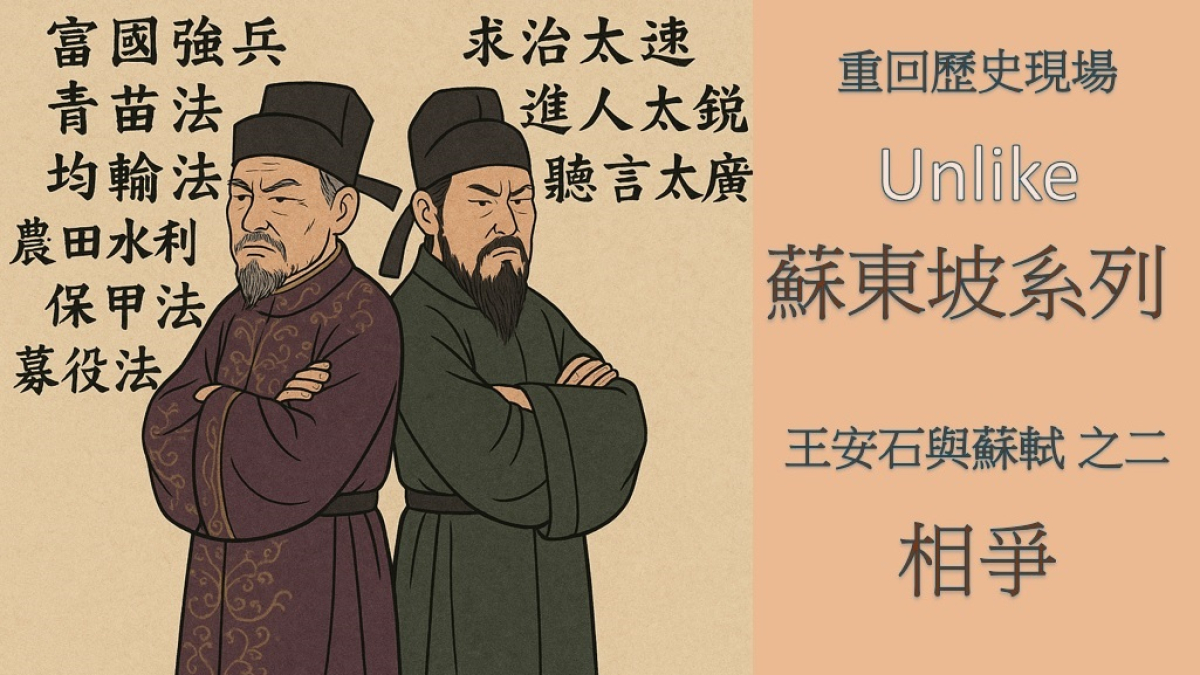如果大家以為當王安石開始推行變法時,便已經和蘇軾勢成水火,爭拗不斷,那就錯了。電視劇中那種在皇帝面前,朝堂之上,舌劍唇槍,爭論不休的情節並未發生過。蘇軾當時的職位仍未達到「便殿議事」的級別,不能經常參加中央核心議論,他能夠與王安石正面交鋒的機會也不多。在蘇軾參加中央決策層之前,王安石拜相之先,兩人未能成為知交,只是個性不同,為人作風有異,不涉及政治上的矛盾。這種相對平靜的關係,隨着王安石開始排擠異己而惡化了。
(二)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爭
蘇軾與王安石的相爭開始於熙寧二年(1069),地點是汴京。
熙寧變法開始的時候,蘇王的關係不算太差。當神宗委派子由(蘇轍)到變法的核心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去幫助王安石時,他没有反對。就是皇帝委派的,若果王安石真的不願意與蘇氏兄弟共事的話,他只需要向神宗說一句,便可以把子由派到其他部門去。據子由自己記述,起初王安石和他在工作上仍是有所交流的,還詢問過他有關發放青苗錢的意見 [1]。當此時,不管是王安石也好,蘇家兄弟也好,誰都不了解誰的政治取向。在王安石方面,他只是不認同蘇氏兄弟的個人禀性,行事作風,但他仍不知道他們對新政的支持度;而蘇氏兄弟對新法仍未有足夠的認識,亦不了解王安石一旦位極人臣之後的架勢。
直至到王安石推行科舉改革時,神宗希望集思廣益,命令各主要官員,一個月內向他提交相關意見書,蘇王的政治衝突才正式開始。
當時蘇軾上了一份《擬學校貢舉狀》,仔細分析了王安石科舉改革的弊端。這篇奏章寫得條理分明,詞文並茂,神宗讀過了之後,馬上召見蘇軾,咨詢他對改革的意見。得到皇帝召見,蘇軾興致勃勃的苦心經營了一篇近萬言的《上神宗皇帝書》,向他分析了當務之急,其中有不少是針對王安石的新政的。於是,蘇軾與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分歧就越來越大了。
這真是歷史上的一大遺憾,本來這兩個絕代天驕也有改變大宋積貧積弱的宏願,卻不能好好地合作。
先是,王安石於嘉祐三年(1058)《上仁宗皇帝書》中說:「內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惧于夷狄」[2];而蘇軾在他的制策中也指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3],他比起王安石所說的,更能點到問題的核心:大宋處在危機之中而毫不察覺。至於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速度,兩人就有很大的分別了。基本上,王安石想利用猛藥,快速根治頑疾,力主富國強兵,他主張「變法」;蘇軾認為,透過調補滋養,漸漸祛病除弊,改變大圍環境,他主張「變革」。這樣的分歧本來可以好好地互相協調的。可惜,他們性格上的差異,造成了不可踰越的阻礙。
王安石是一個自信滿滿的人,「臨事迂闊,且護前非」 [4]。當他向神宗推薦自己的改革大計時,他勸神宗說,諸葛亮不足敬,唐太宗不足羨,惟以上古三代盛世為目標可也 [5]。這不是有點虛無縹緲嗎!他更揚言 「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6]。他的這種一往無前的幹勁 ,真的有點不近人情,難怪他會說:「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7] 。「征誅」?難道為了變法便可以不顧一切,無故殺戮也在所不惜?神宗一朝大獄最多,也許跟這個宰相有關。相比之下,蘇軾提出的方法未必能於短時間之內看到成績,但就整個社會層面來說,較易承受。
後來,王安石越來越感覺到蘇軾的威脅,就多次阻止蘇軾進入決策層。
熙寧二年五月:「(神宗)欲用軾修中書條例。安石曰:『軾與臣所學及議論皆異,別試其事可也。』」[8] 王安石也算老實,坦言自己和蘇軾是没有可能一起工作的,正是道不同不相為謀。不過,神宗想重用蘇軾的心仍未改變,多次試探着王安石,結果王安石如此回答神宗:「軾材亦高,但所學不正⋯⋯且如軾輩者,其才為世用甚少,為世患甚大,陛下不可不察也。」[9]
很明顯,這時期王安石已經把蘇軾視為真真正正的政敵了。可能在他的心目中,就算蘇軾不會威脅到自己的權力地位,他也會威脅到新政的推行,必須要好好處置了他。
熙寧三年(1070),機會來了。謝景温(王安石姻親)彈劾蘇軾為蘇洵守孝完畢回京時,利用官船運貨謀利。朝廷馬上作出大規模搜證行動,搜查範圍達到八個「路」之大(一路就像今日的一省),結果查無此事。蘇軾只是坐了官船離開眉山,搭了一趟「順水船」。那艘船原是去迎接新來上任的官員,所以就順便載了蘇氏一家離開眉山,僅此而已。
這件事讓蘇軾提高了警覺。他一定也思考過:究竟王安石在這件事件中,扮演的是甚麼角色?没有他的配合,朝廷會作出如此大動作來調查此案嗎?王安石是用彈劾之名,行贓害之實乎?最後,蘇軾要求外調以避其鋒。本來以蘇軾的資歷,他外調時應該出任知州(市長)的,但中書省認為不可,只給他一個通判(副市長)的職位。據蘇軾自己揣度,朝中有人恐怕他不肯執行新法,所以不讓他「坐正」[10]。雖然只是外調並不是貶官,但這是蘇王二人關係最差的時期,也是他們最後一次「交鋒」。
往後幾年,王安石與神宗的關係有了變化,神宗不再像從前那樣對他言聽計從。新法的種種弊漏引起強烈的反彈,對新政和新黨的投訴,日復一日的來到神宗面前,這個年青皇帝也不是呆子,他問王安石道:「聞民間殊苦新法。」王安石回答說:「祁寒暑雨,民猶然咨,比無庸恤。」[11] 那等於說,百姓是在無病呻吟。這種話,說過一次兩次還勉強可以,說多了,誰都不會相信。適逢天災頻生,更令神宗不安。還有就是二人在外交問題上的矛盾 [12],呂惠卿的從中挑撥,如此種種,不一而足,令到兩人的互信關係開始動搖了。
最後,一幅繪有當時「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的《流民圖》去到了神宗手中,令他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罷免了王安石。雖然,不到一年神宗便讓他再次拜相,但是,此一時,彼一時了,君臣之間無復當初那種師徒的關係。及後王安石的兒子王雱猝然逝世,他又被自己一手提拔的呂惠卿出賣,讓他受了重大打擊。於是他自動辭職,退出政壇,隱居江寧,不問政事。
王安石退隱之後數年,蘇軾也遭遇了一生中最大的打擊——「烏臺詩案」 [13]。審訊期間,傳聞王安石曾經發聲為他求情說:「豈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14],這段記載未必屬實,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禮為蘇軾求情,確是記載於《續資治通鑑長編》及《宋史》之中 [15]。本來,他們兩兄弟的政見是十分不同的,經過了那麼多政治衝擊之後,兄弟間有所妥協,對當下的政局有一致的看法,不足為奇。王安石已經退出政壇,不宜直接參與此事,由仍是朝官的王安禮來出面最好不過。結果,蘇軾被貶黃州五年,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貶謫。在這五年之中,蘇軾的藝術成就達到了另一高峰,擴古絕今,傲視後世;王安石則潛心禮佛,靜度餘生。兩人遙隔千里,不再聞問。
忽然一日,蘇軾在黃州貶所收到一個叫李琮的「新黨」成員的信。信中李琮傳達了王安石對蘇軾文章的讚賞。就是這封信,促成了二人日後的江寧之會,也是蘇王二人相知的第一步。
(待續)
注釋
[1] 蘇轍《穎濱遺老傳》。
[2]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3] 蘇軾《策略第一》。
[4]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209,英宗治平四年正月卷。
[5]《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
[6]《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
[7]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8]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四,熙寧二年五月卷。
[9] 李濤《續資治通鑑長編拾補》卷七,熙寧三年三月卷。
[10] 蘇軾《與堂兄三首》之三。後來,當蘇軾當上了知州之後,他的確拒絕了執行某些新法。
[11]《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石傳》:「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禮從容言:「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錄錄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眾,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12] 在對遼,夏的關係上,神宗不贊成王安石的策略。
[13] 見拙文《聖主如天萬物春:蘇軾與宋神宗的糾葛》。https://mychistory.com/d001/d0017/ch0002
[14] 周紫芝《太倉稊米集》.《讀詩讞》。
[15]《宋史》,卷327, 列傳86,《王安禮傳》。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Unlike" 蘇東坡系列——蘇軾與王安石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