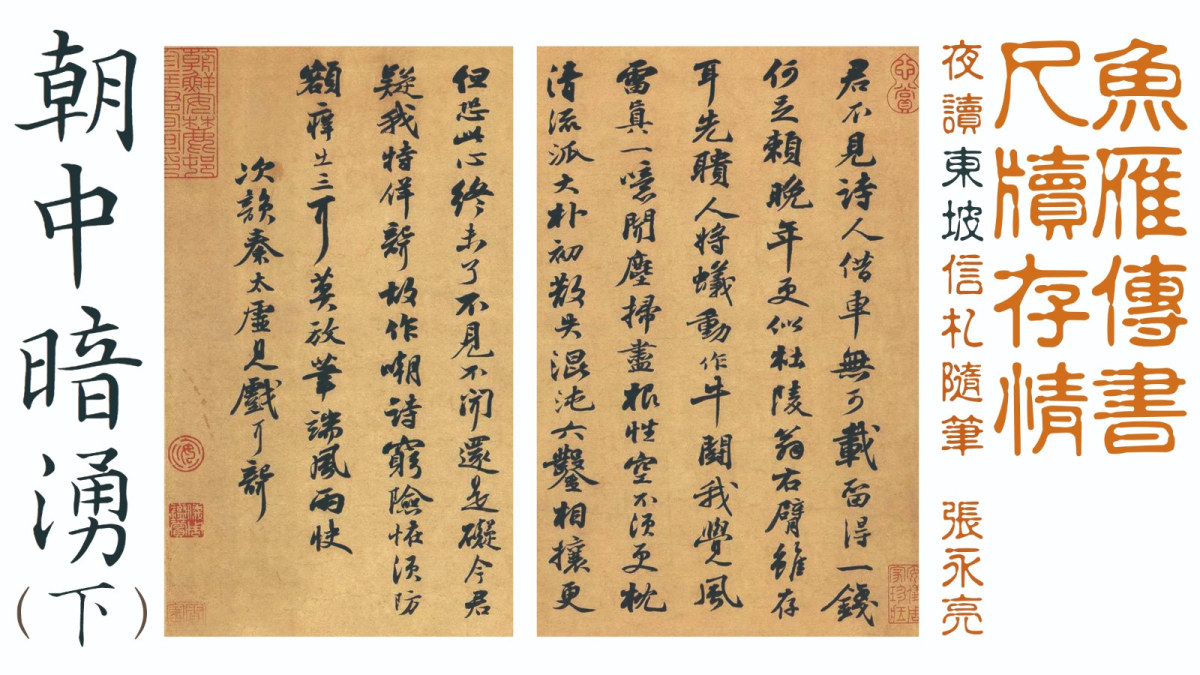第二次在朝
蘇軾48歲(元豐八年,1085),神宗駕崩,哲宗繼位,太后垂簾聽政,司馬光出任宰相。「舊黨」中不少人被召回中央出任要職,蘇軾就是其中一個。
從元祐元年(1086,哲宗第一個年號)開始,是蘇軾的第二個「在朝」階段。這一時期的黨爭比神宗朝更為激烈,更為複雜,除了「新舊黨爭」之外,更有所謂「洛蜀朔黨爭」。事實上,元祐年間,主政的是哲宗的祖母高氏(神宗的母親),政治氣氛經常處於緊張狀態,再加上高氏本人的偏袒,黨派之間更是勢成水火。打從回京開始,對蘇軾的彈劾批評,人身攻擊便已無日無之。之後的兩年,蘇軾不止一次提出過外調[1]。
這次在朝中,蘇軾所遭遇的人事糾葛很是不同。此前,蘇軾遇到的政治矛盾主要來自王安石的「新黨」,這次對蘇軾的攻擊既來自「新黨」,也有來自反對新法陣營內部,包括本來非常看重蘇軾的司馬光及他的「門人」[2]。政見不同,引起爭論,還可以理解,但除了政見之外,官運亨通也成了蘇軾備受攻擊的原因之一。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蘇軾被擢升到內廷要職,皇帝侍讀,不少做官的,窮其一生也未必能達到這些職位,而蘇軾卻在短短的一年之間得此厚遇,怎不令人咋舌驚訝,招來麻煩。蘇軾一點也没有沾沾自喜,反而憂心忡忡:
「某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疏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3]
「⋯⋯某蒙庇粗遣,但躐次驟進,處必爭之地,非久安計,但脫去無由⋯⋯」[4]
蘇軾深深感覺到,接連擢升,其實是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再加上子由也進入了中央權力核心[5],兄弟同列內外廷要職,更易惹人妒忌。
蘇軾能夠高升得如此之快,都是因為高太皇太后對他的賞識。可惜「愛你,變成害你」,高氏把蘇軾推到一個高處不勝寒的處境去,他在給朋友的信中說:
「某江湖之人,久留輦下(京城),如在樊籠,豈復有佳思也。人情責望百端,而衰病不能應副,動是罪戾⋯⋯」[6]
更令蘇軾感到難受的是,在朝中朋友之間竟也暗藏「殺機」:
「自公去後,事尤可駭,平生親友,言語往還之間,動成坑穽(陷阱)」[7]
「風俗惡甚,朋舊反眼,不可覆測,故不欲奉書,畏浮沉爾」[8]
讀者朋友,如果你已經在職場中打滾/拼過十年八載的話,應該會明白蘇軾的心情吧!
勉強要蘇軾應付朝中人事糾葛,實在有違自己的性格。他的本心是嚮往陶淵明式的田園生活的。在給陳季常的一封信中,他便發牢騷說:
「某局事雖清簡,而京輦之下,豈有閑人,不覺劫劫過日,勞而無補,顏發蒼然,見必笑也。」[9]
除了人事紛擾,蘇軾更覺得在朝中毫無建樹,浪費人生。而其他官員,只求政爭不要波及自己已覺萬幸,哪有時間,心情,精力來為國計民生求福祉[10]。最後,蘇軾再次走上要求外任的老路上去。
「⋯⋯又自顧衰老,豈能復與人計較長短是非,招怒取謗耶?若緘口隨眾,又非平生本意。計之熟矣,以此不如且在外也⋯⋯」[11]
第二次外任
蘇軾52歲(元祐四年,1089)時終於獲得批准離京,再到杭州去任知州,進入了第二個「外任」時期。跟第一個外任時期不同,這次蘇軾在每一個州份逗留不久,中央又召他回去,回京後,又被擢升更高的職位,麻煩又更多更大,於是他又再要求外任。如此這般,五年間蘇軾輾轉往返京城和州府之間,風塵僕僕。這時期蘇軾的行程是這樣的:
杭州→回京→潁州→揚州→回京→定州
元祐六年三月(1091),朝廷把蘇軾從杭州召回京任翰林學士承旨。這本來是高太后的好意,但令蘇軾好生為難。如何為難?出任此職之後,他上書請求外調八次之多[12]。我們仿佛聽到蘇軾在說:「太皇太后,你老人家就饒了我吧!」
每次蘇軾要求外任時,都讓人感到他想逃避。的確,蘇軾是在逃避着。他想逃避的是無謂的政治爭鬥,逃避把自己有限的人生斷送在那些於己,於人,於世完全没有好處的麻煩事。他並没有逃避作為一個深受儒家精神影響的士大夫所應該承擔的經世濟民的責任,所以他没有立即退隱,只是把自己可以作出貢獻的舞臺,從中央轉到地方上去。他滿以為離開了京城便可以専心民政,不再惹麻煩:
「某守郡粗遣,去國稍久,矧懷家弟,老病豈不念歸。但聞以眷知之深,頗為當路所忌,縱復歸覲,不免側目,憂患愈深,不若在外之安也。」[13]
「在外之安」可不易得!不久,他便發覺自己的如意算盤打錯了:
「蓋拙者雖在遠外,尚忝劇郡,故不為用事者所容⋯⋯以此,不得不為求閑散以避其鋒」[14]
儘管在外,因為被派的州份較好,也會令人眼紅。他的一舉一動都被人回報朝廷,成為攻擊他的把柄。真的是動輒得咎,為之奈何。這時候,蘇軾年事已高,累了,希望「老境欲少安」[15] 。只求一清靜之處來歇息一下,他也認真考慮到退隱的具體安排:
「然老倦謀退,豈覆以毀譽為懷」[16]
「衰病懷歸,日欲致仕(退休)。既忝侍從,理難驟去,須自藩鎮乞小郡,自小郡乞宮觀,然後可得也。自數年日夜營此,近已乞越,雖未可知,而經營不已,會當得之。致仕有期」[17]
本來的打算是一步一步的淡出政壇,先是離開京師,然後由大的州份轉到小的去,最後再退到為退休(或被貶)官員而設的職位「守宮觀(寺廟道觀)」。怎知,他在潁州待得不到半年便改知揚州,在揚州逗留了半年,朝廷又再召他回去,蘇軾依然是多次要求外調 [18],最後朝廷讓他出知定州,從此不再有「回朝—外任」的戲碼了。因為高太皇太后這時去世了,哲宗親政,朝中暗湧變成了滔天巨浪。
第二次,也是最後一次,貶居
蘇軾57歲(紹聖元年,1094),哲宗罷黜「元祐舊黨」,蘇軾被貶惠州。從這年開始,直到他去世前,他分別在惠州和儋州(海南島上)度過了六年貶謫生活。正是「山兩欲來風滿樓」,對政治氣候的變化,蘇軾早有一葉知秋的預見力, 被貶之前,他已感到自己的仕途有變。[19]
本來蘇軾是希望被派到東南一帶的,朝廷卻把他派到接近邊界的定州去[20]。那也算了,不管遠近,只要離開京師便行。離京前,哲宗給了蘇軾一個警號。按禮節,作為臣子,離京外任,應親自向皇上告辭,才可起行,但是哲宗竟然拒絕了接見蘇軾。好歹也曾經是他的老師嘛!雖然是皇帝,尊師乃是古時十分重視的人倫關係,哲宗居然如此無視此等禮節,可見他對蘇軾心懷怨懟[21]。
故此當蘇軾在定州知道再次被貶時,而且是貶到嶺南,他的心情是頗平靜的:
「某垂老再被嚴譴,皆愚自取,無足言者。事皆已往,譬之墜甑,無可追。計從來奉養陋薄,廩入雖微,亦可供粗糲⋯⋯英州(蘇軾初時被貶的地方,後改惠州)南北物皆有,某一飽之外,亦無所須⋯⋯」[22]
當王定國勸他為自己辯護時,蘇軾斷言拒絕:
「所云作書自辯者,亦未敢便爾。『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23]
三十多年的官場生涯,還辯的不夠嗎?從哲宗對自己的態度,蘇軾是知道自辯也是枉然,何必多廢唇舌。到達惠州後,蘇軾反而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本來就是要遠離中央的,現在不是夠遠了嗎?再加上廣東物阜民豐,又可以享受正宗粵菜(一定比川菜強),還有令他願意長作嶺南人的荔枝,如此好環境,難怪他會說自己「身心俱安」[24]。
他開始在惠州修建房屋,準備把兒孫接來,度過餘生。可惜東坡欲靜,浪濤不息。就在他的新居落成不久,兒孫都來團聚之時,掌權派再次對「元祐黨人」進行迫害,蘇軾一定也感到詫異:都已經被貶到嶺南了,還可以貶到哪兒去?他寫信給王古(當時是廣州知州):
「⋯⋯錄得近報,舍弟復貶西容州,諸公皆有命(其他「黨人」也都再次被貶),本州亦報近貶黜者,料皆是實也。聞之,憂恐不已,必得其詳,敢乞盡以示下。不知某猶得久安此乎否?若知之,可密錄示,得作打疊擘劃也。憂患之來,想皆前定,猶欲早知,少免狼狽⋯⋯」[25]
在信中,蘇軾只希望早點知道是否真的會再貶他處,好讓他可以早作準備。連只求能安心終老也不易得,可哀!
當得知被貶的地方竟然是孤懸海上的儋州時,蘇軾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立遺囑。
「某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昨與長子邁訣,已處置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乃留手疏與諸子,死則葬於海外⋯⋯生不挈家死不扶柩,此亦東坡之家風也⋯⋯」[26]
其次就是安頓家人:
「家累托治下(他的朋友方南圭),無內顧憂思之心」[27]。
蘇軾60歲(紹聖四年,1097)由兒子蘇過陪同,往天涯海角去了。幾經辛苦,才在這個物資匱乏的地方安定下來。想不到地方雖是偏遠,朝中爪牙仍可以伸張至此。原本當地一些好心的官員讓蘇軾住進官舍之中,再將其修葺一番,好讓這個老人家可以住得好一點。這些官員竟因此而遭到彈劾貶職,蘇軾也被趕出官舍。他没有跟長官們作任何交涉,因為他深深知道,這命令必定是由「最高當局」下達的,當地官員也有為難之處。他只好把僅餘的積蓄拿出來,蓋了幾間茅屋以擋風雨[28]。
蘇軾寫給姪孫的一封信最能道出他在儋州的生活:
「老人(蘇軾自稱)住海外如昨,但近來多病瘦瘁,不復如往日,不知餘年復得相見否…旅況牢落,不言可知……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29]
事實上,當時的海南島是「食物人烟,蕭條之甚」[30]。但蘇軾仍盡量令自己適應過來,以注釋經典,追和陶詩,教化鄉民為日常,當然還有就是結交幾個可以喝酒談笑的當地朋友,所以他才會說:「海州窮獨,見人即喜,況君佳士乎」[31]。就在這時,老天爺給蘇軾開了個大玩笑。
風燭殘年的蘇軾,在生活條件如此惡劣的儋州,捱過了三年,仍怡然自得。年青力壯的哲宗,生活在皇宮大內,寒至於涼,暑至於溫而已,卻於二十三歲駕崩。之後,徽宗繼位,大赦天下,蘇軾北歸,也算是個happy ending了。
潮漲潮退,自有常規,想不到,蘇軾的人生際遇也有序可尋。人們總是說「欺山莫欺水」,然而,波濤洶湧,巨浪翻騰,人人視之,自會戒備。危險的是水波不興,暗湧湍流,不在其中,不知其險,往往是善泳者葬身之處。年青時的蘇軾應該也曾以為自己是個「善泳者」,就是知道自己是身處暗湧之中,並未意識到它的危險。到發覺時,已身在囹圄之中。
蘇軾人生中的第一個循環是他的學習期,學習如何看清暗湧所在,如何堅持而不被其吞噬。當他進入第二個循環時,他便可以行止有道,出處自如了。這並不是說他可以做到料事如神,懂得避重就輕,而是他已經能總結出自己的「立朝大節」,做人處事的底線,若然要他越過這一底線,他只好捨棄其他來保存這個「大節」了,為的就是「不改其度」。
注釋
夜讀東坡信札隨筆之十
作者:張永亮博士 旅居澳洲華人
圖片設計:華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