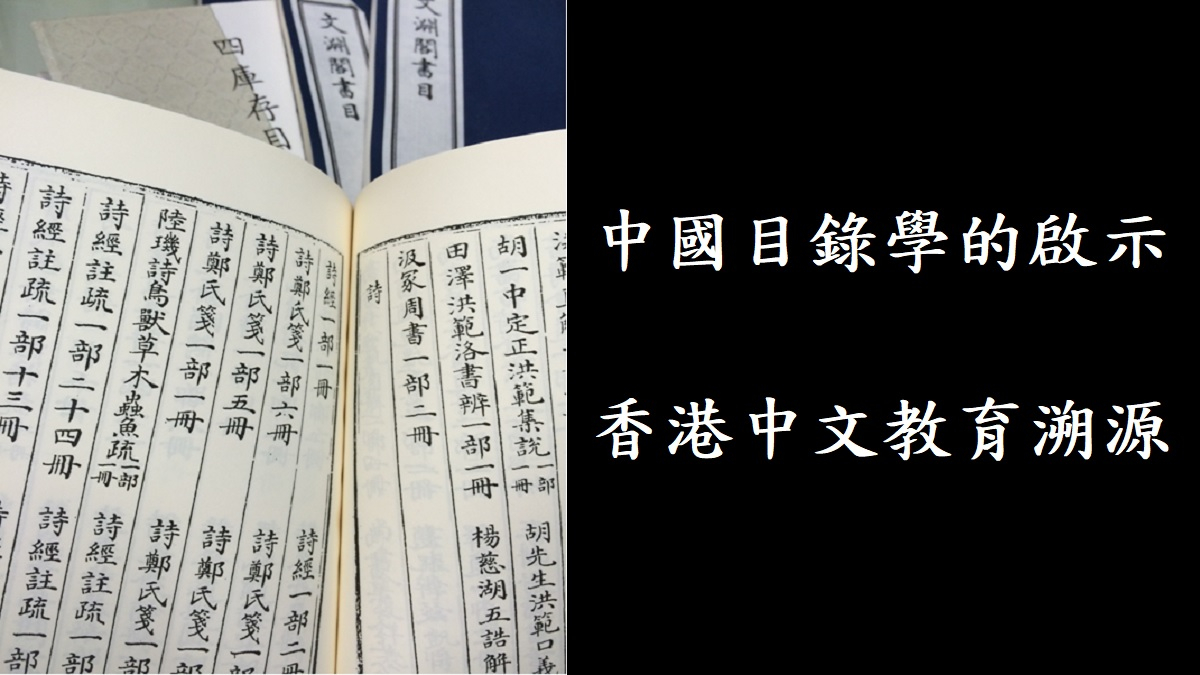近來高中的學生都有這個想法:中文科構成了莫大的障礙,拿取二等的及格級別是不能升上大學的,至少要拿取三等,儘管各科成績突出,考獲五等或以上,但只要中文獲得二等,便於大學門前止步,已有不少師兄師姐遭逢此劫,面對中文科,既恐懼,又討厭,缺乏安全感。作為文史學科的研究者與施教者,看見學生因為中文科考試而討厭了中國語文,怎能不握腕長嘆呢?現在中文科仿佛走進一個迷茫的境界,甚少學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拿取好成績,因為不是下一番苦功就能修成正果,學生不清楚讀甚麼才安心,老師就疲於奔命施教趕進度,大家對此都缺乏安全感,實在有需要回顧課程的設置,並以目錄學為例對其探本溯源。
研究中國古代文史的學者,相信都知道目錄學或文獻學是做研究的必備學問,手上的讀書志、經眼錄、藏書志等各類書目都像字典一樣,伴隨左右,試想想,你研究古典詩詞,沒有一本詩話或詞話在手,怎能成事?目錄學可以是一門非常高深的學問,但最得心應手的還是版本校勘。簡單來說,古人為他的藏書樓編定一本目錄,方便找尋他的書籍,或者政府為國家圖書館編定官方目錄,亦是方便找尋典籍,著名的例子有很多,如《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文淵閣書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藏園群書經眼錄》、《越縵堂讀書記》等等,這些私人或官方編製的書目,部分包含藏書家的讀書劄記,成為目錄學或版本學的研究材料。
朝代興替,家族興亡,都足以令珍貴的藏書消失殆盡,可是餘下的一部目錄,我們便知道那個時候有甚麼書本存世,如果某名人的文集在日後的私人或官方目錄中不再記錄,我們便可以推算那本書何時散佚,甚至比較不同的目錄,作版本校對,研究各種圖書的版本,便可以品評其異同優劣。不過,本文不是探討目錄學的問題,而是從中國目錄中,找出古人的藏書都有一個共識,書籍的子目雖有不同,總目都離不開經、史、子、集。經,主要指儒家的經典;史,即各種史書或典章制度之作;子,是諸子百家的著作;集,是歷朝作家的文集。當然,《隋書‧經籍志》一早把書籍分類為經、史、子、集,這就說明古人所重視的書種,必有此四種。他們的學養就來自這些,多閱讀經、史、子、集,相信不會寫不出好的文章。
從前的香港會考中文課程,雖不為至善,但所包含的除了現當代文學外,還包含了經、史、子、集的元素,隨便舉例來說,〈齊桓晉文之事章〉(《孟子》)和〈論仁論君子〉(《論語》),就屬於經部(以十三經來算),〈廉頗藺相如列傳〉(《史記》)屬於史部,〈庖丁解牛〉(《莊子》)屬於子部,〈醉翁亭記〉(《歐陽修文集》)屬於集部,而古代詩詞亦可計入集部,還有加入古典小說如范進中舉,至於現當代文學一應俱全,別加一篇《漢字的結構》,認識中國的文字形成。於是學生的中國語文能力,就是靠多閱讀這些篇章而見規模,寫作就駕輕就熟了。如果學生再修讀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那就對中國文化有相當可觀的認識。假如在高考認真修讀必修的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再研讀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日後攻讀大學的中文系或歷史系便相對得心應手,之後便可以傳承發揚珍貴的中國語文及文學。
姑不論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的部分,只談中文課程內經、史、子、集的元素,現在學生學習中文感到辛苦,最明顯之處是現在課程講求的是為數不少的評核或能力的“輸出”,當然課程有崇高的理想,可是實情是學生大量做進展性評估,簡單來說,就是多做聆聽,多做綜合練習,多做口試,多做選修單元習作,從各項練習中具體反映能力,使其可以作階段性的評估,務求全方位提升中文能力。可是學生中文差,就一廂情願以為操練試卷不足,於是做更多聆聽、綜合、口試、寫作、閱讀理解等練習,本身缺乏中國語文的基本功,知識輸入少而要求上乘的能力表現,持續操卷,就是入不敷支,只會令學生遭受更多的失敗,失去自信後可能牽連對其他科目的信心,情況悲慘。
從前會考中文課程以閱讀為主,寫作為輔,焦點非常清晰,甚至預科同學都自發多讀中國文化篇章而不是不斷操練實用文或口試,現今中文課程跟以前預科的貌似,設五份卷,就算將要減為四份卷,可是,不見得閱讀跟以前一樣具領導的地位,學生沒有體會經、史、子、集的元素,持續操練試卷或做進展性評估,實在是不按章法的學習中文,情況猶如外國人學中文一樣,學到的是皮毛而不是中國人應學的精髓。所以中文課程內理應包含經、史、子、集的元素,之後在此基礎上加以損益。國學大師就是從經、史、子、集中吸取養份,要提升中國語文能力,可以參考這個方法,而不是由始至終都大量操卷。更不是外行人認為的口語問題,廣東人可以寫出好的中文,好的中文由古至今都不分南北,不妨參考廣東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饒宗頤的文章,加上香港發展出粲然的香港文學,作家屢出,中文的發展完備不言而喻。昔日熟諳廣東話的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到港,着香港大學成立中文系,課程教的就是經、史、子、集。後來許地山再改良經學教育為文史哲教育,其實已包含經、史、子、集的元素,前人的先見之明,即可見一斑,我們在此基礎上改善又有何難處呢?
回想過來,慶幸自己修讀過昔日中學的中文、文學和中史課程,中學的文學和中史老師是筆者的啟蒙老師,及後攻讀本科以至博士,都得力於中學所累積的點點滴滴。相信不少從事文史研究和教學者都有近似的經歷。可是,現在的學生可以怎樣呢?高中中國文學和中國歷史科的課程被削得支離破碎,初中中國歷史科更被部分學校削減課時及強硬地與世史科合併,使中史科的獨立性被削,難以有效讓學生認識本國的歷史與文化,現時更有論者提出仿傚他國詳近略遠的歷史教學模式,需知我國源遠流長而又體系完整的歷史是世界獨有的,學習整套歷史是需要時間和心神的,要對中國的歷史感到驕傲,可以不認識中國孔孟的年代和古代四大發明與科技嗎?中國的文字是古代的國際文字,學生知道嗎?凡此種種,都需要中文、中史和文學科的配合,可是中史和文學科現在處於滅絕的或自然流失的邊緣,中文課程則已面目全非,令人擔心的就是不能把良好的傳統交給下一代。
課程的制定,要貴古重今,不妨參考中國的目錄,篇章用舊的還是新的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古文部分應涵蓋經、史、子、集四部分,這是中國學問的精髓,同時把閱讀視為領頭的一份卷,這才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
香港大學中史碩士同學會祕書麥宇翰
(本文曾於2015年3月《星島日報》「根本月報」專欄刊登,並由「國史教育中心(香港)」授權「知史」發佈,特此鳴謝。)